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!
发布时间:2021-02-06 15:47所属平台: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: 次
摘要: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,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,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。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,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,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。 种类及数量之多,即使置于全
摘要:王阳明“龙场悟道”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,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,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——黔中王门。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,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,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。 种类及数量之多,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。 其中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,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、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,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,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。 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刻,恰好反映了心学新颖思想在西南边地的广泛传播,呈现了黔中王学崛起于边缘区域的生动文化景观,折射出边缘与中心交流互功的复杂历史信息。
关键词:阳明文献 《文录续编》 黔中王门 边地文化 思想传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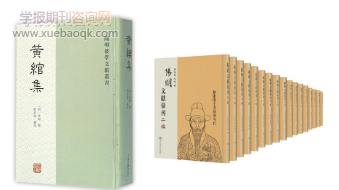
作者:张新民
16世纪下半叶,为配合心学运动在西南边地的发展,黔中王门学者凝聚各种政治与学术资源,先后刊刻了《居夷集》《传习录》《阳明先生文录》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《阳明先生遗言稿》《阳明文录》六部专书,即使较诸王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浙江、江西等中心地区,其数量规模亦足以令人惊诧,不能不说是阳明文献传播史上必须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。
文学方向论文范例:新时代阳明心学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启示
贵州刊刻的阳明文献虽多已亡佚,然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嘉靖十四年刻本及《阳明先生文录》嘉靖十八年补刻本,今皆尚存。 其中《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》(以下简称《续编》)凡三卷,各卷均按文体类别编次,依序为文类、书类、跋类、杂著、祭文、墓志、诗类。 据书后所附王杏《书〈文录续编〉后》,可知书之梓行,乃是因其初至黔,即有感“(阳明)先生以道设教,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,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”; 特别是“(阳明)先生昔日之所面授,此心也,此道也; 今日之所垂录,此心也,此道也,能不汲汲于求乎……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,嘉其知所向往也”。
遂以“《文录》所未载者,出焉以遗之,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,题曰《文录续编》”,以为“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,于道未必无小补。 否则是编也,犹夫文也,岂所望于贵士者哉? ”可见是书之所以题曰《续编》,乃是补已刊的《阳明先生文录》之未载者; 所谓“新刊”云云,亦相对旧刊本《阳明先生文录》而言。 而新刊本《续编》之梓刻时间,亦必在王杏撰文之嘉靖乙未(十四年,1535),是时距阳明先生逝世才七年,谢廷杰之《全书》合刻本尚未刊刻,流传于世之单行本,无不“各自为书”。 《续编》即早期少数罕见单行本之一,历来鲜有史志目录专书著录,即使置于阳明文献整体系统之中,也弥足珍贵。
一、地方王门学者的合作与《续编》的刊刻 [见英文版第5页,下同]
《续编》之梓行,王杏既云乃其“以《文录》所未载者,出焉以遗之”,则主其事者必乃其人,刊刻地亦当在黔省无疑。 考书之每卷卷末,均分三行题有“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”“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”“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”字样,则参与校刻者尚有赵昌龄、陈文学、叶梧三人,后两人为阳明亲炙弟子,否则便不会在姓氏前冠以“门人”二字。 而王杏、赵昌龄亦必为服膺或私淑阳明者,刊刻《续编》一事即足可证明之。 王杏之史迹,综合历代史志考之,知其字世文,一字少坛,号鲤湖,又号日冈,浙江奉化人,嘉靖十三年(1534)巡按贵州。 时“贵州虽设布、按二司,而乡试仍就云南。 应试诸生艰于跋涉,恒以为苦”。 故早在嘉靖初,给事中田秋即“建议欲于该省开科”,然前后逾五年未有定议,至此复“下巡按御史王杏勘议,称便。 因请二省解额,命云南四十名,贵州二十五名,各自设科”。 杏之勘议奏疏明确称:
贵州地方,古称荒服,国初附庸四川,洪武十七年开设科目,以云、贵、两广皆隶边方,将广西乡试附搭广东,取士一十七名,贵州乡试附搭云南,取士一十五名。 永乐十三年,贵州增建布政司,以后抚按总镇,三司衙门渐次全设,所属府、卫、州司遍立学校,作养人才,今百五十年,文风十倍,礼义之化已骎骎与中原等,乃惟科场一事,仍附搭云南,应试中途间有被贼、触瘴死于非命者。 累世遂以读书为戒,倘蒙矜悯,得于该省开科,不惟出谷民黎获睹国家宾兴盛制,其于用夏变夷之意,未必无少补矣。
足证嘉靖年间,尽管黔地“环处皆苗,其冠带而临苗夷者皆土官”,“夷多汉少”的族群生态局面,实际并未完全改变。 但儒家思想的传播范围仍在不断扩大,地域性的士绅阶层早已形成,诚如王阳明《寓贵阳诗》所云:“村村兴社学,处处有书声”,后人据此以为其用心之苦,乃在“喜其向道知方也”。 适可见不仅府州县科考生员的数量日益增多,即独立开科设考亦成为历史的必然。 而正德二年(1508),王济(字汝楫)“巡按贵州,大有声绩,以贵州少书籍,曾与左布政使郭绅刻谢枋得《文章轨范》,以公之士林”。 书稿刊刻前,王阳明受王济之嘱撰序,即称是书乃“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……是独为举业者设耳。 世之学者传习已久,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”。 因而重新刊刻是书,必能“嘉惠贵阳之士”。 当然,他也特别告诫:“工举业者,非以要利于君,致吾诚焉耳。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,类多徇私媒利,无事君之实,而遂归咎于举业。 不知方其业举之时,惟欲钓声利,弋身家之腴,以苟一旦之得,而初未尝有其诚也。 ”凡此种种,在阳明看来,均极不可取。 而主事者王济又尝“谋诸方伯郭公辈,相与捐俸廪之资,锓之梓”。 故阳明又极为担心“贵阳之士,谓二公之为是举,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,则二公之志荒矣”。 尽管“地以人才重,人才以科目重久矣”,但“若作兴风励之机,则在上不在下”,因而“能本之圣贤之学,以从事于举业之学”,以致“风动远人,使知激劝”,仍为多数在黔官员的共识。 即在王济本人,也认为“枋得为宋忠臣,固以举业进者,是吾微有训焉”,用心诚可谓良苦。
由此可见,随着边地科考人数的增多,相关书籍的刊刻也开始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。 《续编》的编排刊印虽较《文章轨范》为晚,但也与大量读书士子文化心理上的需求有关。 《文章轨范》或《续编》的刊行流通,如同科考的独立开设与取名额的增加一样,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宏观治理策略,从地方官员边政实情的观察视野出发,都既可在文化上“昭一代文明之盛”,也能在政治上满足“用夏变夷之意”,从而促使“夷多汉少”的边地朝着内地化或国家化的方向发展,实现王朝中央强化或巩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治边目的。
当然,从国家有意建构的一整套教化体系看,更重要的是,“凡古昔名贤流寓之地,必稽姓氏,为往迹之光,甚而崇庙祀景德,永流韵为人心之芳传”。 如果说稽考流寓名贤姓氏,乃至立碑建祠,使人知所景仰固然重要,则刊刻其生前撰述,从而移易地方习俗风气,影响世道人心,从而改变“理学不明,人心陷溺,是以士习益偷,风教不振”的文化积弊现象,在地方官员看来,当也是其展开教化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。 因而《续编》的刊印作为一种官方政治行为,尚有其他具有地方官员身份,署名为“贵州都司经历”的赵昌龄的参与。 赵氏生平事迹,史籍载之甚少。 考徐问《抚院续题名记》“昔司马文正公谏院题名,有忠诈直回之语,将欲揭诸后之人,俾瞩目警心,聿兴劝戒。 然则今日之求宁,非后事之师乎? 某以是惧,爰命都司从事赵昌龄董工伐石,窃取文正公之意以续书焉”; 王杏《清理屯田事议》“臣巡历贵州新添等卫地方,查据经历赵昌龄呈称,贵州屯种额例……恐虚言无凭,委官履田踏勘,已各得实”云云; 具见参与校勘《续编》者,必是上述两条材料提及之人,则赵氏除参与校对之役外,又曾“董工伐石”,以便刻写贵州抚院续题名,并受命查核“贵州屯种额例”,所报数字均一一真实不虚。 可证赵氏与王杏,二人虽在官秩有为上下之分,多有公务往来,然在私交上亦必时有过从,均心仪阳明心学,赵氏遂深得王杏信任,参与《续编》之文字校订,其名赫然列于书中。
参与《续编》之文字校对者,尚有陈文学、叶梧两人,均阳明早期黔籍弟子,分别署名“耀州知州门人”与“镇安县知县门人”,然其时早已由官任返归贵阳,实际仍以门人弟子之身份,主动承担《续编》文字校雠。 钱德洪《王阳明年谱》“嘉靖十三年甲午五月”条载:
师(阳明)昔居龙场,诲扰诸夷。 久之,夷人皆式崇尊信。 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,主教书院。 士类感德,翕然向风。 是年杏按贵阳,闻里巷歌声,蔼蔼如越音; 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,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; 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。 门人汤、叶梧、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。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,置膳田以供祀事。
席书延请阳明至贵阳,主讲文明书院,其事亦见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:“文成既入文明书院,公(席书)暇则就书院论学,或至夜分,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。 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,不汩没于俗学者,皆二先生之倡也。 ”可见阳明之主讲文明书院,与提学副使席书的关系极大,也可说是地方官员有意支持的一种施教行为,因而参与听讲的生员显然数量较多,汤、叶梧、陈文学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,实乃阳明在黔期间最早的亲炙弟子,亦必列坐于“环而观听”诸生之中。
二、国家边地政治策略与纪念阳明系列活动 [6]
钱德洪提到的汤、叶梧、陈文学等人,因阳明之因缘而知儒家心性学说,晚年致仕归黔带头请建阳明祠一事,亦见于李贽《阳明先生年谱》:“门人汤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。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,立祠置田以供亲事。 ”实际是时“贵阳初设府,未建庙学,权以阳明祠为学,而庙则附于宣慰学”。 故建祠之同时而阳明书院亦得以成立,可证其事之必可信据,则贵阳之建专祠祭祀阳明,较诸直隶巡抚曹煜于九华山建仰止祠祭祀阳明,时间上整整早了一年,可谓全国最早建专祠祭祀阳明的区域,足证边地民众思慕系念之情弥久弥深。 只是无论钱德洪或李贽所记,如果沿流讨源,追溯其原始出处,实皆本于王杏的《阳明书院记》。 王氏在《记》中明白称:
嘉靖甲午,予奉圣天子命,出按贵州,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,予问之士民,对曰:“龙场王夫子遗化也。 ”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,今虽往矣,岁时思慕,有亲到龙场奉祀者,有遥拜而祀者,予问曰:“何为遥拜而祀也? ”对曰:“龙场去省八十里,陵谷深峻,途程亦梗,士民艰于裹粮,故遥祀以致诚云尔。 ”子闻而矍然曰:“有是哉。 ”先生门人汤君、叶君梧、陈君文学数十辈,乞为先生立祠,以便追崇。 余曰:“公帑未敷也。 ”次日,宣慰司学生员汤表、张历等以辞请; 又次日,汤君辈又请。 予曰:“诸君之请,私情也; 问之于官,公议也。 牵之以私者徇,强之以公者矫,矫与徇君子弗取,诸公斯请,情至义得,是可以行矣。 ”乃行布、按、都三司掌印官,左布政使周君忠、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,佥曰:“此舆论也,先生功德在天下,遗泽在贵州,公论在万世,祀典有弗舍焉者乎? 请许之以激劝边人。 ”遂许之。 为赎白云庵旧基,给之以工料之费,供事踊跃,庶民子来,逾月祠成。
文中提到的汤、叶梧、陈文学,以及当时尚为宣慰司学生员的汤表、张历等,显然均为黔籍人士,而受到阳明心性之学的沾溉。 其中之汤,字伯元,即贵阳人,正德三年(1508),“王伯安先生谪龙场,公师事之”,“得知行合一之学”,“正德辛巳成进士,历官南户部郎,出守潮州……甫三月,改巩昌,便道归省。 其在任思亲,有‘肠断九回情独苦,仕逾十载养全贫’之句。 居无何,中飞语归。 ”汤撰有《逸老闲录》《续录》,惜俱亡佚。 黎庶昌撰《全黔故国颂》,将其收入儒林传。
与汤同时之陈文学,字宗鲁,自号五粟山人,贵州宣慰司人,“年十余即能诗,以诸生事阳明,乃潜心理学”,“弘治丙子乡举,知耀州。 三年调简,不果赴。 杜门养痾,一切世故罔预。 稍闲,即与圣贤对……自耀归,日者言岁将不利公,自作《五栗先生志》”。 著有《耀归存稿》《余历续稿》《孏簃闲录》,均合编为《陈耀州诗集》。 后人认为他与汤氏,均“亲炙文成,以开黔南学业,宗鲁得文成之和,兼擅词章; 伯元得文成之正,且有吏治,虽以飞语见责,恬然自退,又何伤哉? ”
同陈文学一样,叶梧(或作“叶悟”)也参与了《续编》的校勘。 叶氏字子苍,亦贵州宣慰司人,正德八年(1513)举人,曾任陕西镇安县知县,刘咸炘撰《明理学文献录》,广搜阳明弟子,“子苍”之名即赫然列于其中。 正德三年(1508)阳明龙场悟道后,讲学龙冈、文明两书院,他与汤、陈文学同时,均为最早进入师门的一批王学弟子,较诸最早在山阴(今浙江绍兴)师事阳明的徐爱(字曰仁),其前后相去不过仅仅一年。 故晚年返归故里筑垣后,不仅与汤、陈文学共同带领地方读书士子请建王文成公祠,同时也与赵昌龄、陈文学合作共同校订了师门的《文录续编》。
汤、叶梧、陈文学三人,外出入仕即为肩负官守职责之地方父母官,可谓握有朝廷权柄大任的士大夫,返黔乡居则为望重一时的缙绅,乃是能够代表读书士子发言的地方知识精英。 而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、贵州都指挥司、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,贵州宣慰司在治城北,贵州布政司、贵州提刑按察司在治城中,贵州都指挥司在治城中西,均同在府城,彼此紧邻。 城内“官军士民移自中土,且因迁调附住于此,生齿渐繁,风化日启”。 故叶梧、陈文学虽名为贵州宣慰司人,实际也是贵阳人。 时王杏恰在巡按任上,按察院具体位置即“在会城东门内”,阳明祠及所附书院也在城东。 据此完全可以推断,所谓黔本《续编》,刊刻地点尚可确定在王杏、赵昌龄、汤、叶梧、陈文学共同交往和活动的区域,即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、贵州都指挥司、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的贵阳,可称为嘉靖十四年贵阳刻本或筑刻本。
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之修建,虽出于汤、叶梧、陈文学等地方缙绅之请,但毕竟要经过代表官方的王杏的允准,并商之“行布、按、都三司掌印官”周忠、韩士英等人,以为可以“激劝边人”,能够强化地方秩序,达致教化目的,才最终得以建成,可视为朝廷官员与地方缙绅的一次重要合作。 而筑本《续编》的梓行,既有主事官员王杏及其下属当差赵昌龄的倡导,也有叶梧、陈文学等地方精英的配合,也可说是地方政府与边地读书士子的一次成功合作,体现了国家治边大员与边地士绅文化共识空间的良性开拓与扩大。 如果以阳明心学在边地的传播和发展为观察视角,进一步向前追溯,则正德三年(1508)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与阳明往复论辩,最终为阳明所折服,并“与毛宪副修葺书院,身率贵阳诸生,以所事师礼事之”,也可说是“身督诸生师”阳明,即以阳明的身教与言教为中介,实现了地方官员与边地读书士子的良性互动。 而阳明亦因此开始传播其与朱子有别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从而培养了以汤、叶梧、陈文学为代表的一批黔中弟子,标志着心学思想在贵州的扎根,汤、叶、陈可称为黔中王门的“前三杰”。 此后更以修建阳明祠及阳明书院为触媒,实现了地方政府与边地缙绅的合作,不仅透过祭仪活动提升了边地士子仰止先贤之心,而且也扩大了有利于边地秩序建构的思想符号资源。
十分明显,《续编》的刊印梓行,与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的修建一样,也是国家行政理性与地方文化认同资源的一次整合,既满足了边地士子阅读心理的需要,也有裨于阳明一生完整思想的传播,遂有孙应鳌、李渭、马廷锡等第二代心学学者的兴起,当被称为黔中王门的“后三杰”。 尤其贵阳一地,“富水绕前,贵山拥后,沃野中启,复岭四塞,据荆楚之上游,为滇南之门户”,不仅在文化风气的开启上具有引领全省的重要作用,即在国家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也有稳定整个西南的战略意义。 地方官员形成了“(阳明)先生功德在天下,遗泽在贵州,公论在万世,祀典有弗舍为者乎”的共识,并与地方精英群体合作刊刻了《文录续编》。 稍后黔中王门学者陈尚象为万历《黔记》撰序,也立足于国家立场着重强调:
今夫天地之元气,愈渐溃则愈精华; 国家之文治,愈薰蒸则愈彪炳。 而是精华彪炳者,得发抒于盍代之手? 其人重,则其地与之俱重,黔盖兼而有之。 贵山富水与龙山龙场,行且有闻于天下万世矣。 世有寥廓昭旷之士,亦必于黔乎神往矣。
这些足证《文录续编》的刊行,与席书要求诸生礼敬阳明为师,王杏采纳缙绅意见修建阳明祠类似,都是颇具国家边地政治策略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。 其发挥了学术、文化、政治等多方面的符号感召力量和影响作用,蕴含着“用夏变夷”即移易地方礼俗的微妙深意。
三、黔地刊刻的多种阳明文献及其源流关系 [8]
阳明著述文献的整理刊刻,即便在僻远的贵州也远不止一次。 王杏《书〈文录续编〉后》便明确提到:“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《阳明王先生文录》,旧皆珍藏,莫有睹者”; 又称“阳明先生处贵有《居夷集》,门人答问有《传习录》,贵皆有刻”; 具见《续编》梓行之前,黔地尚刊刻过《阳明王先生文录》《居夷集》《传习录》等书。 如论撰作先后次第,《居夷集》主要为入黔后之著述,与黔省关系最为密切,结集时间亦最早。 嘉靖《贵州通志·王守仁传》亦明载阳明“正德间以兵部主事任龙场驿驿丞,有《居夷集》传于贵”。 郭子章万历《黔记·艺文志》著录“《居夷集》,阳明先生谪龙场时撰”,亦必为黔中之刊本,均可证王杏之言必不诬。 其刊刻时间,考正德四年(1509)岁杪阳明离开贵阳赴庐陵任,途中曾有信札寄黔中弟子,信中便强调“梨木板可收拾,勿令散失,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,千万千万”。 所云似即指《居夷集》之刊刻,或阳明在黔时即有刻印是书之打算,付梓则必在正德年间后期。 阳明信中提及之黔地弟子达十七人,其中必有参与其事者,当为全国最早的《居夷集》印本。 稍后贵州按察司副使谢东山谓其“读公《居夷集》”,显然又联想到阳明在龙场“百死千难”的情形,“未尝不叹天之所以重困公而玉之成者,实在乎此”。 其寄慨如此之深,似亦入黔获读《居夷集》后才有之文字。 惜书已不传,历来著录者亦极少,然必是最早刊刻之本,似无任何疑义。
《居夷集》今存嘉靖本三卷,首有丘养浩叙,末有韩柱、徐珊跋,丘《叙》云:“引以言同校集者,韩子柱廷佐,徐子珊汝佩,皆先生门人。 ”徐《跋》谓“集凡二卷。 附集一卷,则夫子逮狱时及诸在途之作。 并刻之”。 可识丘、韩、徐三氏,均为是书之校刻者。 惟三人均未曾入黔,其书亦非黔刻本。 韩、徐二人尚在跋文落款处明书“门人”,揆诸史迹,其入门时间必在阳明离黔之后。 故钱德洪特别强调:“徐珊尝为师刻《居夷集》,盖在癸未年,及门则辛巳年九月,非龙场时也。 ”癸未即嘉靖二年(1523),据丘养浩“嘉靖甲申(三年)复孟朔”叙,知“二年”必为“三年”之误; 辛巳则为正德十六年(1521),是时阳明离开黔地已久,故是书决不当牵混为黔本。
继黔刻本《居夷集》之后,黔中尚有阳明在黔遗言专书之锓刻。 主其事者为胡尧时。 胡氏字子中,号仰斋,亦阳明弟子,好与人讨论阳明心学。 郭子章万历《黔记》尝载其事云:
胡尧时,字子中,泰和人,嘉靖丙戌进士,由驾部郎出为云南提学副使、贵州按察使。 公昔为阳明先生弟子,虽职事在刑名案牍,然谓贵阳民夷杂处,宜先教化、后刑罚。 既以躬行,为此邦士人倡。 复增修黉舍与阳明书院,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,悉为镌刻垂远,且与四方学者共焉。 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,即诣阳明祠展拜,如谒先圣礼。 已,乃进诸生堂下,与之讲论学问,率以为常。
胡氏在“民夷杂处”的边地,以秩序的建构为目的,认为“宜先教化、后刑罚”,又鉴于阳明在黔省的影响,遂有一系列的行政作为。 其中搜考阳明在黔遗言,并在贵阳镌刻垂远一事,清人邹汉勋也主动加似证实,以为其“尝师事王守仁,学以躬行为本……又新阳明书院,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,令学徒知所景仰,士风为之大变”。 可证其事必当可信,阳明在黔之遗言,除《居夷集》外,尚另有一胡氏刊本。
胡氏刊行之书,据郭子章《黔记·艺文志》之著录,当题作“《遗言稿》”,或乃《阳明先生遗言稿》之省写。 郭氏按语明云:“贵州按察使泰和胡尧时编集阳明先生遗言在贵阳者,悉为镌刻,与四方学者共焉。 胡,王(阳明)先生门人也。 ”胡氏对阳明的尊崇,观其友人谢东山的赠言:“我国家文明化洽,理学大儒后先相望,而阳明王公则妙悟宗旨,刊落支离,其有功于后学为尤大”云云,或亦可窥而知之,故书名必作《阳明先生遗言稿》,似可完全断言。 是书专记阳明谪居黔地期间遗言,就阳明一生思想发展而言,较之徐爱所辑《传习录》时间断限更早。 然成稿并锓版于何时? 考胡氏到任贵州按察使,乃在嘉靖三十年(1551),则撰稿或当始于是时,付梓则必在稍后。 刊刻地点与《续编》类似,亦当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。 其时去阳明龙场悟道不久,与阳明交往之人或多健在,可说“地近而易于质实,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”,显然具有材料搜考核实上的便利。 其书必多有可观,兼可与《居夷集》互证,惜早已亡佚,难免不令人兴叹。
与《居夷集》《阳明先生遗言稿》一样,《传习录》一书亦有黔中之刊本。 然是书之最早编集,实因徐爱从阳明游久,乃“备录平日之所闻,私以示夫同志,相与考而正之”,遂得以成书。 考阳明与徐爱畅论《大学》之旨,乃在正德七年(1512),而今本《传习录》卷一,亦多载有相关内容,则其书之结集,亦必在是年或稍后不久。 虽规模狭小,不过十四条或稍多,然保存阳明龙场悟道后早朝教言,功亦不小。 以后薛侃据徐爱所载,补以陆澄与自己所录,刻于虔州(今江西赣州),时在正德十三年(1518),是为最早之初刻本,即今本一之上卷。 嘉靖二年(1523),南大吉续刻《传习录》,即今通行本之中卷。 其他可考者,如聂豹有感于其所见之本,“答述异时,杂记于门人之手,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”,乃与陈九川“重加校正,删复纂要,总为六卷,刻之八闽”。 钱德洪广搜师门遗稿,合以诸家之所录,补入其撰辑,重编增刻,时间已在嘉靖三十三年(1554)之后。 故王杏所言专记“门人答问”之黔本《传习录》,必在钱氏之前即早已刊刻。 如谢东山乃四川射洪人,嘉靖十年(1531)举乡试,二十年(1541)登进士,自谓“自弱冠时得公(阳明)《传习录》而读之,虽以至愚之质,亦未尝不忻然会意”,则其所读者,必乃早期刊本。 而蜀、黔两地毗邻,谢氏亦长期关心阳明在黔史迹,则其所读之书,似不能排除即黔本之可能。 因此,尽管《传习录》陆续补辑成书,“四方之刻颇多”,然黔刻本仍为早期罕见之书,透露出不少阳明文献地域传播的信息,惜亡佚甚早,学界亦鲜少知之。
前云《续编》,其书名既冠以“新刊”二字,王杏又明言:“一奉梓《阳明王先生文录》,旧皆珍藏,莫有睹者。 予至,属所司颁给之。 贵之人士,家诵而人习之,若以得见为晚。 ”足可说明黔地必曾刊刻过《文录》,刊刻地点亦必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,惟原版印数甚少,所谓“颁给之”云云,极有可能据原刻再印,否则便谈不上“家诵而人习之”。 足证其亦为官方牵头出资梓行,不仅刊刻时间早于《续编》,即印次亦绝非一次可限。 王杏《续编》接踵后出,实即其书同一性质之补编本。
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《文录》,虽久已不为人所知,幸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明嘉靖年间刻本,书名正题作《阳明先生文录》,凡三卷三册,非特体制规模大小与《续编》相当,即称名亦与王杏所言一致。 而版刻特征虽有差异,风格仍有接近之处。 更要者即与贵阳本《续编》类似,是书卷末亦赫然题有“门人陈文学、叶梧重校”字样,并附有《祭阳明先师文》一篇。 祭文称“隆辈生长西南,实荷夫子之教”; 又云“嘉靖己丑三月戊辰,阳明夫子卒于官,讣闻至辰,门人王世隆等为位设主,哭于崇正书院之堂,复具香币往奠之”。 可证作者必为王世隆,当为阳明生前入门弟子,相互之间多有过从,故一俟闻知阳明讣信,即专设木位祭祀,严守弟子守丧之礼。 具见是书之刊刻,不仅涉及黔地及其学人,更与王门弟子王世隆有关,极有可能即是王杏所说之黔本《文录》。
四、《阳明先生文录》之补刻及其与黔地学者的关系 [9]
《祭阳明先师文》当撰于阳明病卒之后。 按史籍载阳明之卒年,当在嘉靖七年(戊子,1528)十一月。 时王氏(世隆)正在湖南辰州,故获知师门讣闻,已在嘉靖八年(己丑,1529)三月,祭文即撰于是时。 是书既由陈文学、叶梧“重校”,则必与黔地有关。 考明人郭子章《黔记》,果在《总督抚按藩臬表》中有王氏题名,据此可知其字“晋叔,长洲人,进士”,曾任贵州“(按察)副使”。 检读《阳明先生文录》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刻本,恰好有别本不载之阳明《与王晋叔》三通。 首通开首即云“昨见晋叔,已概其外,乃今又得其心也”; 次通又云:“所惠文字,见晋叔笔力甚简健”; 第三通复云:“刘易仲来,备道诸友相念之厚”; 则二人不仅时常见面,同时更有文字交往,从中可见以阳明为中心,其周围已形成一讲学群体,所谓“实荷夫子之教”云云,当为信实可靠之语。
然极为可疑者,王氏里贯既在长洲,万历《贵州通志》所载亦同,长洲乃在江苏,王氏何以自称“生长西南”? 而黔本《文录》与《续编》,一前一后,时序分明,附有王氏《祭文》之书,如若真为黔地刊刻之书,则必有线索可寻。 复核郭子章《黔记》及万历《贵州通志》,可知王氏到任贵州副使时间,乃在“嘉靖十七年”(1538),是时《续编》已刊毕,更遑论更早之《文录》,王氏可能与役? 欲回答上述问题,则必须进一步详考。
先看王氏之里贯,除长洲说外,早出之嘉靖《贵州通志》,便明载其为“辰州人”。 而辰州或称辰阳,故欧阳德亦径称“王君晋叔,辰阳人也”。 其地历来为湖南属府,再查《沅陵县志》,果然内其立有专传云:
王世隆,少英敏,强记为文,援笔立就。 年十七,中正德丁卯举人,嘉靖丙戌进士,授刑部主事,谳议精详,多所平反。 历升贵州副使,有风裁,既归,构大酉妙华书院,集诸生讲业,其中湛甘泉为铭其堂,著有《洞庭髯龙集》行世。
文中提及之大酉妙华书院,乃因大酉山妙华洞而得名,其地即“在辰阳西北”。 其所著《洞庭髯龙集》一书,早已不传,今存《辰州郡城记》一篇,或即其中之佚文。 文中总结辰州形胜,称“据楚上游,当西南孔道”,则王氏所谓“生长西南”云云,显然自有其立论根据。 足证其必为辰州人,所谓“长洲”当为音近致误。 嘉靖《贵州通志》纂成时,距王氏出任贵州副使,前后相去不过十七年,实为当时人记当时事,较之晚出之其他志乘,似更为准确可靠。
王氏既为辰州人,阳明赴谪贵州,往返均经过其地,而尤以正德五年(1510)返程就庐陵知县,滞留当地时间最长,遂多有讲学活动,并“与诸生静坐僧寺,使自悟性体”,从游者则有“冀元亨、蒋信、刘观时辈,俱能卓立”。 所谓“静坐僧寺”,前引阳明《与王晋叔》第二通亦有句云:“守仁前在寺中说得太疏略”云云,其事似均发生在同一地点,即当地虎溪龙兴寺内。 而文中之刘观时,其人“字易仲,从阳明讲学虎溪,尽得其奥妙。 阳明曾作《见斋说》遗之,学者称为沙溪先生”,显然即《与王晋叔》第三通提及之刘易仲。 具见阳明函札之前二通,必当作于其在辰州时。 第三通有语云:“路远无由面扣,易仲去,略致鄙怀,所欲告于诸友者,易仲当亦能道其大约。 ”其时阳明已离开辰州,似当撰于滁州督马政送别观时之后。 阳明尝自谓“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……久之辞归,别以诗”,诗中有句云“秋风洞庭波,游子归已晚”,足可征而证之。 故王世隆与冀元亨、蒋信、刘观时,亦必在正德五年(1510)初,阳明离黔途经辰州时,得以面益入师门,遂形成楚中王门早期重要人物群体。
再论黔本《文录》之刊刻,《续编》既云“新刊”,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必为旧刊,时间当在嘉靖十四年(1535)之前。 然王世隆嘉靖十七年(1538)始任贵州副使,何以能与黔人陈文学、叶梧合作,提前预刻是书? 陈、叶二氏之所为,亦径称“重校”而不云“校”? 实则王氏之到任副使,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《文录》旧版尚存,而王氏似有可能获见其他异本,遂据以补刻,分置于各卷之后,痕迹宛然犹在,均不难辨识。 例如,《与王晋叔》三通,虽为阳明旧文,亦必乃王氏私藏,复加上其私撰《祭文》一篇,或如钱德洪所预知,乃“好事者搀拾”,虽文献价值极高,仍为补刻时羼入其中者。 其时王杏已离任,陈、叶二氏仍告老乡居,遂聘其就旧版重校,或有个别挖改,为官绅之再次合作。 与王杏刻本《续编》一样,补刻重校地点亦必在贵阳。 而王氏以副使身份与陈、叶二人合作,就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补刻重校,其书以其到任次年或再次年推之,亦当称其为嘉靖十八年或十九年贵阳补刻本。 以补刻重校耗费时间相对较少而论,似可即定其为嘉靖十八年贵阳补刻本。
转载请注明来源。原文地址:http://www.xuebaoqk.com/xblw/6210.html
《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》